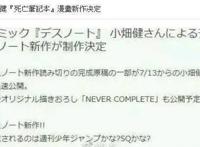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12)
2024-01-14 来源:旧番剧
济慈-雪莱纪念馆济慈写下的最后一首颂歌是《秋颂》,作于一次秋日漫步之后:这个季节多美啊——天空多么晴朗。一种温和的凛冽。真的,不开玩笑,纯净的天气——月神的天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喜欢收割后的田野——胜过春天那清寒的绿意。不知为何,那收割后的田原看起来是温暖的——就像有些画给人暖意……(济慈致雷诺兹,1819年9月22日)一年后的早秋,他从伦敦南下,于晚秋时抵达罗马。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秋天大多在海上度过。他有没有错过那“重重薄雾和果实圆熟”?《秋颂》是一首如金秋一样丰美的诗。诗的前两节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丰收时节的斑斓秋色:累累硕果,姗姗繁花,嗡嗡蜂群,满满粮仓,还有最后榨出的滴滴果浆。其中“收割”与“粮仓”的意象应和着一年半之前那首十四行诗《每当我害怕》中的诗句:
每当我害怕自己将不复存在,
而我的笔还未及收割我丰产的心田,
堆积如山的书本尚未如富足的粮仓,
在字里行间贮藏成熟的谷粒。
死亡的威胁与尚未实现的艺术理想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也许正因如此,济慈才尤其喜爱那收割后的田原,虽然土地上残留着短短的残梗,似乎毫无美感,但没有什么被荒废,也没有什么未达成。第三节则在秋景的基础上配以阵阵秋声,从视觉转向了听觉,一如华兹华斯的《永生颂》,在“辉光逝去”之后,诗人仰赖听觉去感知那精神的浩瀚水声:
春天的歌儿在哪里?啊,在哪里?
别去想春曲,你也有你自己的音乐,
当一道道云霞让渐黯的天色绚丽,
当收割后的田原染上玫瑰般色彩浓烈;
这时,小小的蚊蚋以悲哀的合唱
在那河畔的柳树之间发出哀鸣,
随轻风的起起落落而升升潜潜。
成熟的羔羊在山边啼叫嘹亮;
蟋蟀在树篱中歌唱;红胸的知更
以柔美的高音在花园里歌咏;
而成群的燕子在天空中呢喃。
但蚊蚋的和声是哀悼的。知更鸟也高吟冬的讯息。燕子集结,准备南归。在一切达到丰实之后,自然转向萧瑟。诗在离别中收场,“艺术的终极是平静”(希尼,《丰收结》)。
然而南下的济慈最终没有迎来新的春天。1820年11月30日,他写下最后一封信。如他在信中所说,他不善于告别,“总是鞠下尴尬的一躬”。在此期间,他没有给芬妮写信,也不敢拆开她的来信。他的医学知识让他对自己的症状洞明而悲恐。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杰里米·泰勒的《神圣生死》。1月28日凌晨三点,日夜照料他的塞文为了让自己清醒,为病榻上的济慈作画。这是一幅不忍多看的肖像:枕头上的济慈阖上了往日那双“好奇的眼睛”,面色苍白,头发凌乱,汗水湿透。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个黑色的晕影。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119/204732_3468.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323/220014_9253.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520/145510_58010.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420/115226_611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