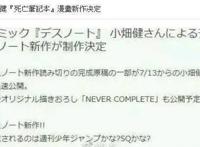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6)
2024-01-14 来源:旧番剧
《角斗场》,乔万尼·保罗·帕尼尼绘,1747,沃特斯美术馆浪漫主义诗人对废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残缺、碎片、废墟构成人生的核心。生命本身就不完美。过程远胜于结果,求索的行为本身大于求索的目标,比如雪莱永远攀登那永远攀升的高峰,阿拉斯特梦中的追寻,老舟子和哈罗尔德的漂泊,施莱格尔所说的“追求无限”,施莱尔马赫那“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求”。在诗歌形式上,浪漫诗歌中有许多“未完成”,如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雪莱的《生命的胜利》以及济慈的《海佩里翁》系列,开启了十九世纪初以来相当规模的“片断”诗。或许,济慈也从那些残损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中获得启示。海顿在日记中写道:上周一,一千零二位访客参观了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大英博物馆成立以来访客最多的一次……我们听到两个相貌平平的体面人互相说道,“它们是多么残缺不全啊,是不是?”“是啊,”另一位说,“但是多么像生活本身!”
残缺即人生。1818-1819年间,济慈创作了两部雕塑风格的史诗《海佩里翁》与《海佩里翁的垮台》。这是济慈继《恩底弥翁》之后的又一次史诗尝试,但却比上一次困难得多,这与他同期的大量阅读和关于“诗性人格”的思考不无关联。两部作品都是片断,前者体现弥尔顿传统,后者则似但丁的《炼狱篇》。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谱》记载,海佩里翁是十二位泰坦旧神的一员,是天(父)地(母)之子。济慈这两部史诗大致讲述泰坦诸神与奥林匹亚诸神新旧交替之际的身份危机。《海佩里翁》的笔触冷静,没有个人介入,没有道德说教。整体基调不仅折射出1818年滑铁卢之战以后英国的精神状态,更隐含诸多自传色彩,比如济慈对恶疾的不祥预感,自身家世的败落,以及他作为医学出身的诗人的诞生,甚至那些静谧的景物描写也让人想起济慈童年的生活环境。《海佩里翁的垮台》则延续着《睡眠与诗歌》中关于诗人天职的思索。
先来看《海佩里翁》。诗歌始于“悲伤的山谷”。失去天国、坠入尘世的泰坦诸神仿佛失去了“真我”,既不解自己的命运,也怀疑自己的身份:
我消失了,
离开了我自己的胸膛:离开了
我强大的身份,我真实的自己,
处在王位与我在此静坐的
这抔尘土之间
然而,这位绝望的天神依然希冀东山再起,他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反问道:
难道我不能创造吗?
难道我不能赋形?难道我不能塑造出
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119/204732_3468.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323/220014_9253.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520/145510_58010.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420/115226_611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