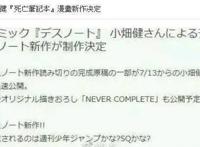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8)
2024-01-14 来源:旧番剧
“消极能力”可以看作对“恭顺能力”的发展。两者都强调自我的谦卑、顺服乃至消解,以便更好地表达对他者和未知世界的共情。济慈传记的作者W. J. 贝特曾这样解释“消极能力”:在我们充满不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体系或一个公式能够解释一切;甚至,用培根的话来说,语言也至多是“思想的赌注”。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颗善于想象并且开放的心灵,以及对复杂多元现实的高度包容性。然而,这涉及一种自我消解。(W. Jackson Bate, John Kea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3, p.249;另可参考Bate的Negative Capability: The Intuitive Approach in Keats, Contra Mundum Press, 2012.)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消极能力”的“消极”暗示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消解”,这是实现共情、自我超越的前提。大约一年后,济慈在信中提到“诗性人格”,也是对“消极能力”思想的进一步阐释:至于诗性人格本身……它并非它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它毫无个性……在所有生灵中,诗人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身份——他始终在塑造着——或填充入其他某个身体——日、月、大海、男人、女人,这些有冲动的生物富有诗意,因为他们拥有不变的属性——诗人没有,没有自我——他必然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中最无诗意的一个。(济慈致理查德·伍德豪斯,1818年10月27日)
济慈关于“消极能力”和“诗人无自我”的思想与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论人类行为的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Actions: the Natural Disinterestedness of the Human Mind)中提出的“人类心灵之天然无私无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十八世纪的“同情性想象”传统密不可分。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认为,海兹利特所说的“disinterestedness”并不排斥所有的私利或功利,而是敞向未知的多元(Hazlitt:The Mind of a Criti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0)。济慈的思想主要在这个意义上与之发生交集,并将之运用到创作层面。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119/204732_3468.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60323/220014_9253.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520/145510_58010.jpg)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Juliet [DVDrip x264 AC3][10bit](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版)(GONZO 2007)[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420/115226_611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