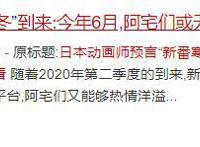对谈丨《海上凡花》与上海疫情中的基层妇女(4)
2024-09-29 来源:旧番剧
叶子婷还分享了她2014年还在读博士时从荷兰来到上海做外来务工方面的质性研究时产生的思考,当时她的采访对象有工厂女工、美发美甲从业者和家政阿姨,她发现访谈结束后自己就离开了她们的生活,对她们的访谈成为了自己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己对她们的生活完全没有贡献。作为一名研究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国内女性的学者,她觉得如果拿着她们的分享就离开,那么自己也会成为剥削者之一,所以希望等到毕业之后有能力的时候能够帮助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从学术出发,是可以动员到不同的力量进行互动互助。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严海蓉也在回应中探讨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她从自身1990年代末在城乡调研经验出发,谈到当时以博士生身份在农村做调研时,农民们希望她作为知识分子能够为他们代言,帮他们去反映农业税费的负担等问题。这种信任与她个人品质无关,而与她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身份相关。而在城市调研时,这种信任需要慢慢建立,一旦建立之后,当时的很多打工妹也相对容易敞开心扉。但是一些年之后,基层社区对于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基层居民开始感觉到你们来做调研是为了自己写论文,不太容易给予信任。严海蓉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反思,她认为自延安时期开始大批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一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入了一个“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建立了一种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多年后仍然有所保留。
当她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下乡时,发现那时农民对知识分子依然怀有着信任。后来基层民众感觉到一些学生学者是把他们当做数据采集的对象,社会的共同性消失,他们感受到被客体化。有观点认为基层对学生学者的态度转变主要是因为基层民众发现知识分子无法帮他们解决问题,严海蓉认为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使认识到知识分子无法切实帮助解决问题时,基层民众中还有一些人愿意保持信任、关系和感情,为什么呢?这当中,知识分子自己的定位有一个转化,就是把基层民众的问题变成我们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这种“共同关心和共同面对” 转变了常见的研究者和被访者的主客体关系,这是信任和情感关系的基础。
章羽以2022年上海疫情中的切身经历解释了对于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研究为何重要,身处疫情的上海民众每天为抢菜、团菜和居家办公而时间贫困时,接到外地朋友因看到新闻而打来的慰问电话时,既感动又无奈。感动于朋友的关切,无奈于他们的执着而无法理解身处现场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章羽提到的一些例子证明了在场体验的意义和价值。当将来有一天我们回望这个事件时,身处其中的我们的所见所闻和体验经历就构成了理解现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进入当下,记录当下”也是《海上凡花》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就像一句歌词中说的,“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那样,我们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就是借用上海工人新村的阿姨们的眼,带着我们领略疫情下她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她们的不易和坚韧,以及透过她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普通百姓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信心。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