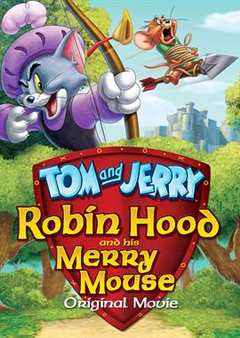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2)
2023-12-21 来源:旧番剧
一、提出先秦乐钟一钟双音的见解,从而使学术界对以钟磬之乐为代表的先秦音乐文化,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58年,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出土,为试奏乐曲,一钟双音,初展声容,但当事人仅作偶然现象对待。1977年,由吕骥同志率领他与王湘等分赴陕、甘、晋、豫四省,进行了一次至那时为止涉面最广、含量最大的音乐文物普查,对新石器中晚期以来的陶埙和商周两代的钟磬做了大量测音。这次普查对他的学术生涯乃至对音乐考古学的影响,也许只有到世纪之末、回首百年学术史时才能给予充分认知。测音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乐钟正鼓部内侧与侧鼓部内侧留下调音锉痕,而且注意到这两个部位铸有凤鸟图案。这一现象引起普查小组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位乐律学史研究者,他探求、思考这一现象的角度和着眼点在于:不是把一钟双音作为一件乐器的发音现象解释,而是把乐钟正鼓、侧鼓部实有音高,放到一套乐器应该形成的音阶结构中去观察。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中,他把数十套编钟的音阶一一排列,那如同环链、严密成序的音阶组织,便展示了只有一钟双音才不致使音级隔断的结构。
一钟孤鸣,难成音序,于理相悖。对散布覆盖在相当区域中、相当套件编钟的综合观察,将偶然现象放到它应处的乐律学内部规律中,其中隐含的音列结构和由此而生的一钟双音的规律性便清晰起来,做出科学解释的时机亦即成熟。他大胆推测道:“如果说殷钟的右鼓音还只是钟乐音阶发展初期的一个‘征兆’,那么西周中、晚期的乐钟右鼓音就已经在发展过程中被整理成序了。”“其音阶组织的严密,已不容许偶然性的东西存在。”
翌年,刚刚出土的曾侯编钟正、侧鼓部刻写的阶名,证明了他的科学推论。但乐律学上的规律是否能成为物理学上的规律,仍然受到人们的怀疑。中国科学院陈通、郑大瑞同志的声学研究,最终解释了瓦合状钟体两个基频互抑的物理现象,从而使这一埋没了两千年的、体现着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科学发明重现于世。
当这一发现及其理论验证被学术界普遍承认之后,他却多次说过:一钟双音现象,实际上是物理学界解释声学原理、考古学界提供铭文实物、乐律学界研究音阶规律,三者结合、缺一不可的集体成果。三相帮衬,俱著声名,不能功归一人。对在这项音乐史、考古研究领域里重大发现过程中,他所处的首倡先声的重要位置,他从未在文章中居功自诩。
作为一位严肃的史学家,学术上的创建,不仅需要开拓者的洞察力,还需具备一项成果在经历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招致传统习惯抵制的勇气。一钟双音的提出,曾遭到包括他的业师杨荫浏先生这样卓越的音乐史学家的怀疑,直至曾侯乙墓发掘之后,杨先生还对他说:“以后不许这样冒险。”语气中虽然包含着对后学的垂爱,但毕竟反映出一般人对新说所持的态度。为此他说:王国维谈到,凡作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并借宋词章句,诉其苦情。其一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三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根据自己的特殊体会,他补充道,作学问还有一层风险,即如辛弃疾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所云:“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恶俗×KNA×紫音】[妄想学生会/黄段子学生会*(第二季)][Seitokai Yakuin Domo 2][02][720P][简体][MP4][bt磁力种子]](/images/loading.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