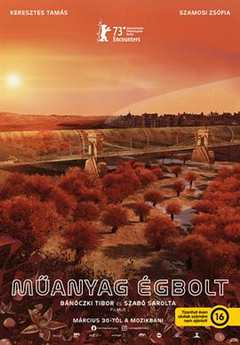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6)
2024-06-15 来源:旧番剧
作为开西北旅行写生风潮之端的艺术家,赵望云对民族形式的讨论非常自觉,他写道:一、他是否体验过西北原野的秋天趣味。二、对西北农民的生活是否有深刻的认识。三、他所用的工具是否适用于他的技巧。四、他的绘作技术是否已臻达于成熟阶段。……如果某画家能克服了这些难题,我想我们的绘画上“民族形式”的问题,或可以在他的作品成功上得到结论了。
赵望云对“民族形式”的思考集中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媒介及技巧两个方面。第一,在他看来,民族题材探索的首要问题是要深入边疆。有关这一点,华芬也提到,“如果我们不把民族文艺错认为狭义的优越民族的文艺,就必须扩大我们作品的内涵,反映地方性,反映边疆人民的社会生活”。郑君里在吴作人“用浓郁的中国笔色”描绘中国山川人物的作品中望见了“中国绘画民族气派的远景”。第二,赵望云重新提出了笔墨问题,指出了线条的独特价值,并认为线条是中国画的基本骨干,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表现技术,他进而谈道:“为了倡导‘民族形式’的时代作风,是需要把它在新技术上加以应用的。”吕斯百也认为:“由不同的技巧和工具材料,由不同的形式,来探讨适合于我民族性的内容与途径。”题材拓展也带来了艺术语言探索及审美价值的重构。
图4 星廓《哈萨克人写生》,
源自《雍华图文杂志》1946年第1期
西行艺术家的实践拓宽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视域,边地与边民充实了边疆题材的内容,更开拓出了一个语言、作风与审美的新方向。艺术家对民族性或民族形式的探讨,还有另一个更为隐蔽的线索,即“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在全球图景中对中国的重新理解与定位。无论是受左翼评论界的影响以彰显“中国作风”,还是嵌套于中西对举的世界主义框架,民族形式的讨论都离不开更为宽阔的全球脉络。诚如张安治所言:“美术虽具有最大的世界性,亦同时具有深厚的民族性。”
“民族形式”探索中暗藏着在全球语境中凸显中国“独特性”的诉求。艺术家不但借此展开现代性探寻以回应民族主义潮流,并尝试寻求民族艺术的特性以重塑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身份。诚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和新颖之处在于全球性的体制变革,“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其他(包括历史的)共同体的表述,甚至与之交锋”。正是在与其他认同彼此竞争互动之时,民族性问题才凸显而出。有关民族性或民族形式的提出不单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而且还将中国放置在了一个更大的全球视野中。左翼文艺界的论述将中国放入世界范围内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中,新文化运动者将中国作为“西方中心”的一个边缘地方,在民族主义者的表述下,中国则是与西方并置的另一个中心。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艺术家而言,西北边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景观、族群面貌和历史遗存成为重塑现代中国特殊性的场域,比如在吴作人的探索中,西北边地成为他折中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一个利器。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