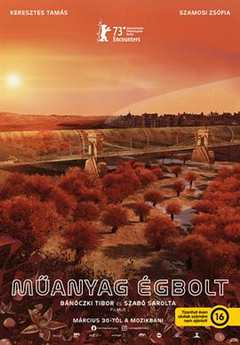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5)
2024-06-15 来源:旧番剧
二、形塑国族:边疆题材与民族形式边疆题材的兴起是艺术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自觉吸收边地文化、凝聚多样族群的内在结果,这一题材在“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上拓展了现代中国的视域,深入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过程。宋祝平认为,“我们自认为古老文化,不过是一些上层阶级的文化,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民族的灵魂”,在他看来“边疆的土地是我们的土地,边疆的民族是我们的同胞,边疆的文艺在我们的文艺里,应该占多大的一个位置”。他的论述一方面凸显了边地族群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边疆与边地民族的阶层属性,边疆题材所代表的底层、民间与文化多样性。1947年,张汉光在《论边疆文化国族化》中亦有专门的论述:
第一是今日的国族文化,不是中原民族独创的文化,而是国内各民族文化混融的结晶,现在却正在积极地现代化。第二国族化不是汉化,是国族底现代化,旨在发扬边疆固有的优良文化,提高边疆文化生活水准,以便加速国族文化现代化,第三是文化国族化,不是地方或民族便没有自决自治的权利。
张汉光认为国族文化应容纳不同族群的文化,注意地方特征与各族群特质,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现代化的。国族这一概念的接受与孙中山的主张有关,其包含着融合国内各族,建立民族国家,实现领土保全与国家统一的诉求。20世纪40年代对所谓国族文化的讨论,在艺术上集中表现为对“民族形式”的探索。
民族形式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3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揭示出了“民族”与“中国”间的关联,同时激发了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尽管左翼文化界主导了这场讨论,但民族形式问题引发了更多文艺人士的思考,如张安治就注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艺术在新旧与中西之间的取舍,以及“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大众化美术的诉求亦构成了民族形式思考的另一个脉络。
艺术家所关注的重心是实践而非论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背景下由都市向边地的流动潮流中,西行艺术家将目光进一步延展到边地世界。在民族形式的探索中,边地、边疆民族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实际上边疆题材既为“民族形式”之主体——民族国家,拓展了实体与内涵,也丰富了艺术家的表现主题,更带来探索艺术语言新变的契机,最终汇入“民族形式”的探寻。这首先展现为对边疆题材的发现和重视,其次是对艺术语言的本土化探索,最后则是通过多族群重塑中国身份。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