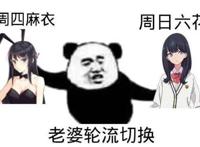周之桓评《花衣魔笛手》|“杀死”传说(5)
2022-10-26 来源:旧番剧
”(118-119页)从十一世纪末开始,欧洲便发起了持续两百年多达九次的十字军东征,由基督教士兵组成的军队希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突厥人等手中收复地中海沿岸原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地区,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并保护基督教朝圣者。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儿童。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宗教信仰使得儿童盲目地结伴外出“冒险”。在阿部谨也看来,父母难以养育孩子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传了下去,一代代人铭记着生活所带来的悲痛。“后代的人在各自时代的社会、思想状态中接受这一传说,根据内心的要求而改写这个传说。”(140页)而由于流浪乐师的身份在近代早期以前被人们所排斥即歧视,加上学者们也用这种眼光看待他们,吹笛人便慢慢被引入了故事之中。(164页)“追寻传说变化的方法只要一个。即注释诸种讨论、争议背后翻涌的各种人的动向,并评价在此之中的传说变化。”(178页)阿部谨也从近代早期的各种人物日记、碑文及教理问答等材料中将饥荒、瘟疫与吹笛人等元素联系到了一起,在1565年左右成书的《席莫伯爵编年史》中,捕鼠人首次出现在了“哈默尔恩的130个孩子失踪传说”之中(191页)。同时在欧洲各地,如巴黎、波罗的海小岛、奥地利的科尔新堡等地也出现了“捕鼠人”(196页)。正如德国学者斯潘努斯(Spanuth)所指出,“吹笛人”是将“捕鼠人传说”与“130个孩子失踪传说”融合在一起的关键点。“吹笛人”与“捕鼠人”在“当时的身份制秩序中二者完全没有区别”(205页)。阿部谨也不仅仅跟随着当时最新的研究转述给读者,并加上自己的分析,来讨论传说的变容,还展现了自己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人文关怀:
在社会底层呻吟挣扎的民众的痛苦,如果用语言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就过于逼真,在出现的那一刻便被民众认为是虚构的故事。正因为处于痛苦的深渊,所以民众在无意识之中过滤苦难,以超然的形式将其浓缩在一则传说中。(210页)
“杀死”传说的历史学家
当读者与阿部谨也一同进行着侦探游戏,不断接近着传说真相的同时,兴奋感也在最后变为了感慨。传说在历史学家的手中被抽丝剥茧,越接近真相,传说也越接近死亡。正如开篇所引用的《鲁迅诗话》,文人将原本来自于民间的诗词占为己有,作为文人骚客的专利,久而久之,脱离了社会生活,越弄越僵。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将传说当作自己的研究,越接近真相,传说也失去了魅力,最终“杀死”了传说。但历史学家还需要避免另一个陷阱。阿部谨也敏锐地提醒道:“将传说作为民众精神的展现而礼赞就会被政治利用,基于课题意识或者使命感高涨而进行传说研究则使其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最终成为悲伤小丑。”(241-242页)这似乎成了传说与民俗研究乃至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大难题。无论是罗马帝国晚期蛮族与民族大迁徙研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盛行,还是法国学者对古代高卢的构建,都是如此。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