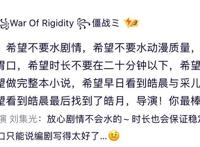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18)
2022-11-05 来源:旧番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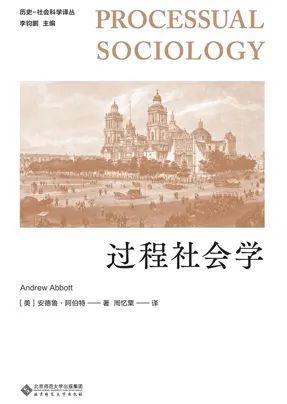
《过程社会学》,[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周忆粟 译,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这两年你也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对性/别议题相关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有一段时间,其实时常能看到你的身影。
黄盈盈:
我确实很少对新闻事件发表即时评论。我们很多时候容易把一个原则性的、理念性的讨论,或者把一些结构性的、总体性的认识直接嫁接到对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这会丧失对于事实的基本了解,这点对于公共讨论是非常不利的。我不是说这些理念与认识不对,是说不能直接对等于每个具体的案例。生活千姿百态,也纷繁复杂,但是概念往往是抽象和理想型的。我的基本训练是,就具体的事件来说,如果没有对基本“事实”的了解,不好做评论。当然,当下有没有去了解“事实”的现实条件,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我写过《大时代与小田野》,社会调查的政治性,躲不掉。
新京报:我想起在《论方法》中,两位老师提到“元假设”是调查问卷的灵魂(“灵魂”即生活是光谱式的存在,而一切界定都是我们的人为)。如果一切界定都是人为的,你如何理解社会调查中的“真实”?
黄盈盈:
即便经过后现代的洗礼,我们对于本质性的“真实”“事实”会打问号,但是对于社会调查中“真实”的讨论,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潘老师退休之后,我从他手里接过两门课,一门是性社会学,一门是方法课。这两门某种程度上是一拉一推,都会触及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性社会学它和很多热点事件有关,它同时和你的情感、价值、道德判断非常相关,现实感、切身感都很强。而方法课则是要把情感性和立场性的东西往后拉一下,它要让你去看你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或者说元假设是否立得住,你的论点所依赖的论据在哪里,你的资料收集是否多维,是否可靠,资料之间的互证性和关联性如何,你的分析逻辑是什么,等等。要让你看到数据、故事的制造过程,各个环节可能的问题,以及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两门课开篇都会说,首先不会去看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观点是其次,重要的是你的观点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可能受到哪些理论脉络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方法学训练的一个意义所在。同时,方法训练也要讲求资料的复杂性,包括其社会性与政治性。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天真的社会学家。这个材料摆在你面前,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事实。要认识到资料所附着的层层灰尘,或者说认识资料之间的矛盾张力,各种套路,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贴近你所关心的现实/真实。某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多维、多重的真实。你看到的可能是其中一些有限的面向。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