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成为“后人类”,为何依然如此惧怕它?(6)
2024-06-15 来源:旧番剧
《未来50年》,【美】 约翰布罗克曼 著,李泳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却大都将商业运作下技术进步与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图景相结合,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狭隘的「后人类」的惶恐,仿佛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第二天就会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这种错觉一方面来源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区隔(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在上世纪中叶观察到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正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缺乏对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敬畏,并未试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实际进展,反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肌理,急于将表面的状况纳入到其熟悉的问题域(典型如伦理、艺术、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中进行分析,如是得到的多半不是学术分析,而是天方夜谭。
诚然,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想要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许日益困难,甚至可说是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我们仍需要寻找、培养那些可靠的能够沟通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人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追踪技术发展的进程,弥合不同领域的裂隙,守望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意义上,那些急于对最新技术进展发表看法的学者并没有犯下根本性的错误,只不过少了些进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纪科幻作家们通过「故事」与「预言」来达成警告的行径。然而距离奥威尔、赫胥黎与迪克等人的作品问世已有几十年历史,我想我们早该迎来更加扎实可靠的融合多个学科知识的后人类研究,而不是不断重复那些先辈早已讲过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体,
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了?
「总有一天,」乔愤怒地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推翻你,推翻你们自动服务机的暴政。人的价值、怜悯和温馨将回归社会。」——PKD《尤比克》
如果要迎来一种更加扎实可靠的后人类研究,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脱离狭义的技术的限制,还原「后人类」概念最初丰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后人类」问题的核心是对现代世界中异化的人性的恐惧与反抗,这种异化总是来源于一种「非人」的「客体/物」,因此后人类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对客体/物的恐惧」。以最容易理解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如基因编辑、脑机接口与优生学的结合)为例,基因编辑意味着将人改造成了「非人」,脑机接口则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这两种具体技术与优生学的结合则进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体」对人的替代或统治——整个逻辑并没有脱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Seed-Raws] 儘管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尽管如此世界依然美丽 Soredemo Sekai wa Utsukushii - BD-BOX (BD 720p AVC AAC).mp4 [補種][bt磁力种子]](/images/loading.g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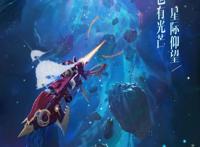

![20yrs ago - [1999-2000] Imaboku_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地的我,超時空幻境,今、そこにいる僕)_TV[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80911/090839_1989.jpg)
![20yrs ago - [1999-2000] Imaboku_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地的我,超時空幻境,今、そこにいる僕)_TV[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90429/145208_6175.jpg)
![20yrs ago - [1999-2000] Imaboku_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地的我,超時空幻境,今、そこにいる僕)_TV[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190728/110608_5684.jpg)
![20yrs ago - [1999-2000] Imaboku_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地的我,超時空幻境,今、そこにいる僕)_TV[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0421/093751_3011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