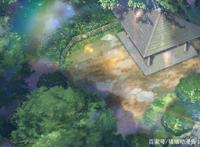历史永远不会真的抵达终点:福山与“后真相”时代的欧美思想界(7)
2022-10-26 来源:旧番剧

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戈里耶维奇·杜金,他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倡导者
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不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会卷土重来。认为民族主义会再次撕裂欧洲,即是认为集团间的争执是永恒的,外敌的消失会将矛盾转为内斗。三十年后,人们发现历史没有重复,却在押韵,这便是福山在特朗普时代写下的《身份政治》的内容。在冷战的终末,福山站在普遍主义的历史高原上,指出普世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体两面,对小到婚姻家庭,大到集体主义的一切共同体都有潜在破坏力,同时也感到集体认同的渴望对普世主义构成威胁,却不能预知将来的集体认同会采用何种分界线。
问题不在于福山是否高估了1991年末冷战结束的历史意义,他只是反映了后历史的心智。这种心智在全球化时期蔓延至各个角落,包括1992年初之后经济腾飞的中国。福山本人却更谨慎,他认为未来将有“史后世界”与“历史世界”共存。他认为政制受文化影响,对后苏联的波兰的预期比对俄罗斯更乐观。而今的后见之明发现全球化只维持了一代人,冲突的新边界只东移了一千公里。其实将民族主义等身份政治视作较坏的政治形式,不仅是普遍主义者的观点,也是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亚历山大·杜金在90年代就预言过英国民族主义将疏远欧洲、美国的种族冲突会愈演愈烈,这位新欧亚主义者主张利用这些分裂并培植仇恨,同时打压俄罗斯内部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会疏远潜在盟友。杜金以分化欧洲的设想,需要在催化西方的撕裂的同时保持俄罗斯的地位,这必然失败,因为给他人的心灵下毒者,在最初的一念间就最先毒害了自己。
如果将目光回溯到久远的过去,就会在但丁等古人那里找到普世帝国的观念。福山的历史终结后美国将失去美国性,末人的宿命是没有记忆的时间黑洞,而杜金的欧亚主义却是逆练麦金德的结果,和大地神话的政治表达。若要问是什么让福山的普世主义明显区别于杜金的帝国主义,将后者视作偏见剔除出去,并让当今“帝国主义”的词义更像是扩张的民族主义,这便是理性在历史中的长期作用,它是世界历史变迁中真正不可逆的部分。然而,如果他认为历史的终结不是意识形态的寂灭而是“最后的意识形态”的永存,就忽视了现代与但丁时代的区别。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