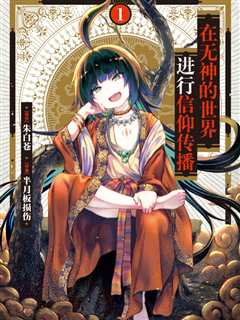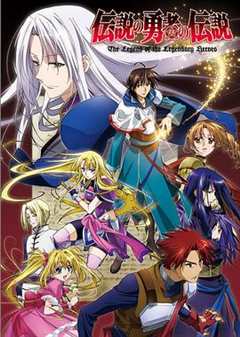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7)
2023-06-03 来源:旧番剧
”其所积淀的深厚“宗教”观念,也为其后扩大内涵奠定了基础。三、正祀、正祠
与淫祀、淫祠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社会中存在有正统的组织宗教与非制度的民间信仰之分,其区别的主要象征乃体现在不同的神明信仰与仪式行为之中,祠庙便是神明之所寄,于是祠神(分正祀与淫祀、正祠与淫祠)也就成为研究者讨论的热点。赵世瑜曾就此提出中国自宋以后有两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可以作为“精英宗教”与“民间宗教”区别的观点:一是礼与祀,二是正祀(包括杂祀)与淫祀。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是把“祀”放在“礼”之中,合乎礼的祀就是“正祀”,否则就是“淫祀”;而与礼相应的范畴是“法”,与礼相对的范畴是“俗”,淫祀或民间宗教就是属于“俗”的范畴。笔者大体上赞同这一说法,但“礼”与“祀”似乎不是对立的范畴。李安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就对《仪礼》和《礼祀》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指出:由周代所制定的礼制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这个礼可以说是包括了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仪式和政令等;
它的大可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也包括了日常所需要的物件;可以说“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据《礼记》所载:“祀”只是“礼”的一部分,“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谓“礼有五经”,即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种,祭祀则属于吉礼而居五礼之首。据此,笔者认为有“正祀”与“淫祀”作为主要相对范畴即可。
“正祀”与“淫祀”是否即官方(或国家)宗教与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之二分对立关系呢?现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既有对立又有互动,但笔者认为无论对“正祀”或“淫祀”都不宜以静态观念去套析,而应从其动态流变去探究。
首先,祭祀对象与祭祀主体者互不可分,在《礼记·曲礼下》和《礼记·祭法》中又都各有其具体规定:合乎礼而纳入祀典的就是“正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周代行宗法制,祖宗之庙祭属于大典,其规定十分细致,王、诸侯、适士、官师与士、庶人,都有严格的区别,但也并非只针对士、庶人实也指向王之下的各级贵族而言。如鲁国大夫季氏曾擅自到泰山去祭祀,他把正祀、淫祀的界限冲破了,引起了《论语》之非议。这种界限不清,直到秦汉时期仍如此。
秦汉时期全国有形形色色的神祠,周振鹤曾指出:这一时期祭祠对象十分广泛,有多种自然神、动植物神、人神、厉鬼、仙人以及灵物、灵像等,“几乎无神不有祠,无神不致祭”。这些神祠一部分是前代遗留,更多的是新创。秦汉统治者又特别热衷于鬼神之祀,加上方士的成仙鼓吹和播弄,“许多神祠随时随地而立,不少民间信仰也变成国家宗教”。蒲慕洲对秦汉时期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之论述更为全面而具体,他列举秦汉一些君主对神祠限制并不严格的情况,如秦始皇规定:“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汉高祖十年,有司请令“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汉高祖还在长安设置了来自各地的巫者。汉武帝好求神,立神君,任意将民间人物纳入官方宗教系统之中,后来《汉书》均以“罢淫祀称之”。王莽即位后所立新制度,“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一千七百所”,《汉书》也以“鬼神淫祀”称之。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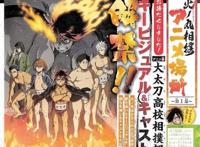

![【国漫】山河社稷图 第8集 先诛怪鱼又落水底 寻宝之路遥遥无期 1080P[bt磁力种子]](https://wimgs.jiufanju.com/thumbnail/2020/1118/162551_127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