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现代巴黎的忧郁诗人(8)
2024-06-15 来源:旧番剧
《巴黎的忧郁》忧郁,对波德莱尔来说,几乎就代指了美的发生,生命的复活,以及世界的运转。正是忧郁,掌控着惊人的力量,推动着整个世界的新陈代谢和荣枯变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说,他有一千多年的回忆,而忧郁就占据着一千多年回忆的核心。在常见的阐释里,忧郁常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安、痛苦、自我否定,这一脉从浪漫主义一直延伸到现在。在现代性的经典论述中,忧郁集聚在焦虑、分裂、歇斯底里、创伤之中,它无法真正浮现,但却被认为是普遍的。波德莱尔的忧郁别有不同。为了回应资产阶级的荒谬境况,福楼拜的做法是,保守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面,有规律地生活,以滋养作品,使其拥有暴力和独创性。从表面的意义上看,波德莱尔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从未有过有秩序的生活,也从未展现过对规律和秩序的焦虑。但就对资产阶级的简单想象的抵抗上,两者确是殊途同归的。实际上,简单而外化的忧郁,是一条不归路,尽管它非常及人,非常普遍。
但是抽象到极简的忧郁形象,也似乎成为波德莱尔最被认可的形象之一,但却和真实的波德莱尔相差甚远。让-保罗·萨特所想象的波德莱尔就是这样的,但同样缺少了父亲在场的萨特也很难再想象出别的波德莱尔的形象了。在萨特看来,波德莱尔的生命是一个缓慢解体、崩溃、痛苦的过程,从青年时代到最终逝世,波德莱尔更加忧郁了,他所有的才华都只剩下了回忆。萨特将波德莱尔比拟为何蒙库鲁兹,这是《浮士德》笔下的小人精,这个小人寄生在封闭的烧瓶里。波德莱尔,又一次遭受了巨大的误解,他被看作是停滞者,背对未来,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持吝啬的姿态,不想效力,也无从效力。“人们经常谈到波德莱尔的柏拉图主义或者他的神秘主义,好像他渴望挣脱自己的肉身束缚以便如《会饮篇》中描写的那样面对纯理念或绝对美。事实上,我们在波德莱尔那里找不到为神秘主义者特有的那种努力的丝毫痕迹。
因为那种努力,必与彻底放弃尘世和非个人化相伴。假如说他的作品中无处不见对彼岸的思念、不满足和对现实的超越,他却总是在这个现实的内部自怨自嗟。对于他来说,超越从围绕他的万物出发,指示自身的踪迹,画出自身的雏形;甚至万物必须待在那里,以便他能有超越它们的乐趣。”
萨特显然无法理解诗歌的存在方式,诗歌以湮灭来复苏,以沉默来高亢。正如波德莱尔在《不可补救者》中所表达的,“变成自己的镜子的心,/这就是明与暗的相对!/摇曳着苍白的星光的、/又亮又黑的真相之井,//含讥带讽的地狱灯塔,/恶魔的恩宠的火炬,/唯一的安慰与荣光,/——这就是’恶’中的意识!”诗歌的忧郁,不同于现实中的镜中的忧郁,也不同于面容和身体上的忧郁。如果说,面容的忧郁只是浮浅的外观,它沦为文化研究的边角料,那么镜中的忧郁则是影子,它的发生机制是黑暗来临,影子自现。而诗歌的忧郁,则像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它由无限的闪烁所构成,并在空无中萤萤发光。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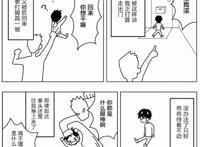
![[VCB-Studio] Suzumiya Haruhi no Yuuutsu / 凉宫春日的忧郁 / 涼宮ハルヒの憂鬱 10-bit 1080p HEVC BDRip [TV MOVIE Lite Ver Fin][bt磁力种子]](/images/loading.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