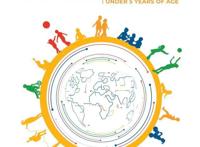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标准?(17)
2024-09-29 来源:旧番剧
其三,是否以成本核算的“专业性”塑造执法队伍。精算执法人员的成本收益到每分钟,就不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去向上级展示执法队伍的政治忠诚。执法队伍的政治性来自专业性;执法队伍缺乏专业人员的荣誉感/羞耻感,也就不具备政治性。其四,是否重视在行政区和商业区执法而忽视在居民区执法。居民区的执法公正系着民心,是城市秩序的基础,其重要程度远高于浮在表面上的行政区和商业区秩序。居民区不是法外之地。若公共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车,社区内部和周边的人行道上就更不能停车。优质的社区自治和自治契约需要效率极高的综合执法队伍支持。
任性地使用公权财力,精英与平民就会分裂,内聚力和外部吸引力就会降低,技术与知识创造/应用的环境就会恶化。所以,精算使用公权成本与收益的程度,能展示政权的理性或任性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进步的第二标尺。
(三)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如何对待育小、养老,是当代社会进步方向的根本问题。在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而且还在膨胀的项目分别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卫生、社区建设和社会治安。换言之,公共支出主要涉及育小、养老,即劳动者再生产。政府随经济发展提供公益,精算公共开支的成本收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如何看待育小、养老的成本核算。
大都市是国家财富和税收的主产地。由于基础设施越来越先进,吸引的人口越来越多,不动产也越来越昂贵,生活费用水涨船高。都市市民最主要的恐惧和痛苦来自不可避免的生育和养老负担,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前景感到恐慌,是大都市最重大的公害。由于城市居民的育小、养老必然向上看齐,生活就必然越来越艰难。在市场竞争机制主导的经济大环境里,为维持正常的劳动者再生产,不断减轻广大市民的痛苦,由政府主导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均等化,使之与家庭货币收入逐渐脱钩,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也是第三大原因。
首先,自古以来,劳动者再生产主要由个体家庭承担,辅之以血亲家族内的互助,政府时以政策干预,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世纪初开始,经济领域保持由市场主导,社会领域却呈现去市场化的总趋势,即政府组织全社会共同分担育小、养老的责任。公立学校成为基础教育甚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所有政府都以各种途径深度干预城市住房市场,使之趋于均等;公民按人头缴纳均等费用,由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系统和免费医疗系统。到21世纪,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已渐成发达国家公认的“民权”,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者基本的共同诉求。世界各国促进育小、养老趋于均等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大原则一致,即由个人、集体、各级政府分担。极端遵从市场机制的新加坡政府,为93%的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分配保障,也是极端。
猜你喜欢
动漫推荐
免责声明:动漫番剧数据来源网络!本站不收费,无vip,请勿上当!
www.jiufanju.com-旧番剧